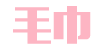最好的声誉!今年海南电影节力作大卖
栏目:成功案例 发布时间:2025-12-11 10:32
 第七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昨天落下帷幕。 《桑格豪森的森苏特/七月魅影》(Sehnsucht in Sangerhausen / Phantoms of July)作为“金椰子奖”主竞赛单元评审团获奖影片之一,以独特的情感质感成为今年最受影迷观看和喜爱的新片之一。近十几年来,德国导演朱利安·拉德迈尔不断借鉴历史文献、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前卫电影传统,为当代德国电影构建了一条独特的思想路径。尤连的长期合作者兼制片人基里尔·克拉索夫斯基也出现在每次美学实验中,提供他的创意作品。女主角克拉拉·施温宁凭借上一部作品《美丽的地方》获得2023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节最佳女主角金豹奖。他是德国新一代演员中的耀眼面孔。当代德国电影研究者张超群(以下简称RC张)对三位主创(简称朱利安、克拉拉和基里尔)进行了万字的深度访谈。谈话从《Sehnsucht》和德国故乡桑格豪森(Sangehausen)的诸多传统开始,扩展到鬼魂、移民、托洛茨基、诺瓦利斯和爱森斯坦未完成的《资本论》计划。逐步揭示影片背后复杂的思想,系统审视搞笑又深思熟虑的整体创作过程。 “Sehnsucht”的修辞:德国浪漫主义与大众文化 RC 张:在《桑格豪森的Sehnsucht》标题中,“Sehnsucht”是一个非常特定于德国文化的词,无法准确翻译;而国际英文标题《七月幻影》则指向了一个略有不同、更加幽灵般的形象。 2006年,Valeska Glitzbach还拍摄了一部名为《Sehnsucht》(Sehnsucht)的电影,同样发生在德国东部。哈夫你看过这部电影吗?朱利安:所以,是的,我知道那部电影。瓦莱斯卡还被认为是柏林学派的院长,并在 DFFB 任教。我对他有一点了解。我也知道《渴望》这部电影,因为我在2006年左右开始拍电影,当时我搬到了柏林,开始学习电影。这些电影当时正好在电影院上映,我就是在那时开始接触它们的。张RC:您在这些电影中寻找什么样的“Sehnsucht”,它与纯粹的浪漫或怀旧欲望有何不同?朱利安:所以我认为它是由多种因素自然产生的。首先,我并没有打算拍一部关于《Sehnsucht》的电影,这并不是我最初的想法。但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创造的人物慢慢开始呈现出一种严峻的状态。然后我在研究的时候,很快就发现,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其实出生在桑格豪森附近的一个小镇,他就是你在德国想到的那个能写诗的作家。最常谈论“Sehnsucht”这个主题。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这将成为电影的主题。这样,我之前写的和这种地理背景上的联系就会自然地结合起来。另外,我并不特别介意Valeska的“向往”,因为“Sehnsucht”这个概念在德国很常见且众所周知,并不是一个很新奇的主题。我喜欢“Sehnsucht in Sangerhausen”这个标题的原因是因为它听起来像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它有轻微的流行、流行歌曲的品质,我认为这很有趣。这个词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含义。更严肃的层面上,我认为这可能与德国的一种政治欲望有关,比如对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渴望,对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的渴望,或者对超越资本主义剥削的生活的渴望。但也是一种更经典、更浪漫的感觉,就是想象没有哈维的另一种生活ng具体定义它是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类型的定义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中。我发现有趣的是,虽然“Sehnsucht”这个词可能有一点听起来流行、“廉价”的含义,但它实际上具有内在的政治潜力。 “我想去别的地方”这个非常普遍的愿望,实际上隐藏着一种对德国现有社会结构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当然,我不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政治来解决,它会保持沉默,但我喜欢的是这个词有一个现有的尺度,汇集了不同层次的感受和思考。我想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我在想的另一件事是我可能想在这部电影中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以前的电影更多的是一种图案化的布莱希特结构,或者更系统的、类似模型的结构。在那些电影中,有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感觉,但那并不重要。这次我想探索这些非常个人的情感,看看这些个人情感与政治问题有何关系。张RC:为什么国际片名不延续这种兴奋,而是用《幻影》?朱利安:然后是关于“幻影”这个名字的问题,正如你提到的,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词。在不同的国家你必须找到新的翻译方式。还有一个问题是“桑格豪森”这个地名太不为人所知,以至于人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小镇。名称 所以这是一种妥协。经销商和销售公司都表示这个标题很难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我认为“七月幻影”对于 mempromiso 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这有点遗憾,因为原始德文标题中明显的地理参考缺失了,而且我喜欢德文标题中的“Sehnsucht”让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在寻找什么。也许你是什么king在英语中是“幽灵”而不是具体的感觉。但我喜欢这种对比:七月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月份,每个人都成年了,而“幽灵”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七月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月份,所以也许“七月的幽灵”有某种有趣的层面。张RC:“在你看来,‘Sehnsucht’和‘Heimat’有不同吗?有一些说法认为这两种情感可以相似。但看了你的电影后,我觉得‘Heimat’不是那个概念,对吗?”朱利安: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确实是我不喜欢的浪漫德国派。这种浪漫主义最终成为德国本身的一部分——就像德国灵魂的“Sehnsucht”。我们的想法是将这种情感和浪漫主义从德国的概念中解放出来,让每个人,甚至移民、韩国人、伊朗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情感,而不是局限于德国灵魂的想法。这样我会更国际。从文本到场所:一条新的创作之路 张瑞成:您之前的作品,比如《Blutsauger》或者《一条资产阶级狗的自我批评》,与历史文本、马克思的资本、苏联文学和前卫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您第一次在“地方”工作。您如何描述这一变化?从桑格豪斯出发,您带来了哪些新东西?朱利安:是的,没错。我感受到了我以前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我可以复制自己并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并变得更糟,或者我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就像你说的,我以前都是从文本、非常抽象的概念开始,然后在现实中寻找抽象的概念。一致的东西。但这次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地方出发,一个小镇。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一条从物质到概念的路径。过去,我是从具体的物理现实开始,然后转向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对观众来说也更真实,比如我自己。其中有对诺瓦利斯的《蓝色花朵》的参考,但这些参考自然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我仍然对理论和理论问题感兴趣,但此时它们更多地是反思问题的工具,而不是首先的起点。张RC:同时,在写作过程中,这座城市是“正确的”还是你在剧本中重塑了你最初的愿景?小镇是从头开始重塑剧本吗?朱利安:是的,这绝对是真的。事实上,在我来到这个小镇之前,并没有剧本。当我来到这里时,整个事情就开始了,然后它就不断发展。通常,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镇,都会坐在咖啡馆里。我首先看到的都是女服务员,我想:在这样的小镇上,女服务员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然后我想,我来自柏林,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在这里遇到女服务员会怎么样?然后我注意到附近有一个音乐会场地,我想也许他们会成为音乐家或者某物。就这样,一切开始成形。我还记得米洛什·福尔曼的电影《Lásky Jedné Plavovlásky》(1965),讲述了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女人爱上了一位音乐家的故事。我想也许这里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故事。晚上晚些时候,我去了另一家披萨店,发现所有服务员都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北马其顿。在镇上散步时,我还看到阿富汗难民和越南移民居住在这里。这让我意识到很多关于东德的德国电影都没有表现这些移民的存在,就好像移民不存在了一样。即使在佩措尔德的电影中,你也几乎看不到不是德国人的人。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不是我生活的现实世界。 RC 张:这次看电影的时候,我特别被桑格豪森的雕像、纪念碑和公共雕塑所感动。它们似乎不仅仅是背景,而是像重新引用的现成文本,带有当地历史、政治和美学的痕迹。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意识地将这些雕像作为一种新的“引证系统”来替代以往作品中文学或理论文本的引用?朱利安: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市不再有原来的工业了,整个工业都消失了,经济因此陷入衰退,失业率很高,人们处境尴尬。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雕像似乎让我们想起了该工艺曾经辉煌的历史,它们带着一种幽灵般的存在,仿佛过去仍在荣耀现在。这些雕像并不是为了庆祝“美好的过去”,而是提醒我们过去的痕迹仍然存在于现在。 改写德国现实:前东德的移民与日常生活的鬼魂 RC 张:你把拍摄地点设定在前东德,我注意到影片中角色的母亲曾经在负责电影材料的德发工厂工作。这样的设置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朱利安:是的,桑格豪森附近有一家工厂叫奥尔沃胶片厂(东德胶片原料制造商),负责胶片材料的生产,这些胶片的应用非常广泛。我不确定它是否出口到苏联,但它为许多国家制造了胶片。有一本关于这家工厂的很好的书,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员工都是女性,而且当时的工作是手工的。阅读这些女性如何掌握自己的工作并在电影制作中培养出自豪感是很有趣的。我们的电影也是用胶片拍摄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向他们致敬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揭示了另一个层面——参与该项目的许多音乐家都来自西德,对东德电影文化并不了解。所以这个设置确实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例如,乌苏拉的父亲开玩笑说,东德电影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她母亲的心意。米斯特里和电影技巧。我非常喜欢这种在电影课堂上工作的视角,因为电影背后总有一些人在制作素材:不仅是导演和摄影师,而且这些工人也看不到。影片后来提到了一位女演员,但西德人并不知道她是谁。这也反映了今天的现实:这种文化的历史几乎无人知晓,西德人对东德文化兴趣不大。张RC:这部电影受到苏联或东欧集团电影的影响吗?朱利安:是的,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那就是基拉·穆拉托娃的《漫长的告别》(1971)。我们关注他如何使用相机——他的动作、移动、变焦和平移——令人着迷的是他要做的事情有多少:相机可以是静止的,但通过变焦和平移,他仍然能够创造出一种极其复杂的视觉语言。我们真的很佩服他的这种方法电影 - 在同一个镜头中从大型特写镜头转变为广角全景镜头,利用动作来创造惊喜、节奏和情感变化。这个方法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正在看的另一部作品是乌兹别克斯坦导演埃利尔·伊什穆哈梅多夫 (Elyer Ishmukhamedov) 的《兰宾》(Lambing, 1967)。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我们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电影语言,可以说,我们确实从它那里“偷”了一些东西。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乌兹别克电影很精彩,但伊什穆哈梅多夫的名字太难记了,我总是记不住,而软电影绝对值得一看——我强烈推荐它。张RC:我发现在你的很多电影中,音乐在章节变化之前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往往具有非常德国的交响乐的品质。看起来这部电影主要是由音乐组成的。 Footor 你选择了这首音乐吗?它们有什么隐喻意义吗?朱利安:在这部影片中,音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想用德国浪漫音乐,尤其是罗伯特·舒曼,他也来自东德,来自这个地区。但更重要的不是地点,而是我喜欢的钢琴曲的天真行为。它被称为“von Fremden Länder und Menschen”(von Fremden Länder und Menschen),是舒曼的“Kinderszen”(童年场景)的开篇章节。就像一个孩子想象着遥远的地方,想象着陌生的人,想象着另一种世界——我觉得这种氛围很适合这部电影。它很简单,但却具有深厚的情感深度,我喜欢这种平衡。另外,为了与“德国高雅艺术”、古典音乐形成对比,我还想要一些具有类似情绪但格式相同的流行歌曲。我们找到了真实存在的当地民歌,甚至是关于我们拍摄的小镇的歌曲,我们把它们收集起来。我发现这种对比特别有趣,我喜欢这种方法。后来,我直觉地觉得需要一些更神秘的东西。我想到了笛子,因为在仙女中,笛子常常象征着魔法师c,就像在某个地方打电话给你。我偶然听到了日本作曲家武光彻的一首作品,觉得非常完美。起初我很担心,我对这首音乐到底了解多少?这有道理吗?但后来我发现他还有我们用过的另一首曲子,那是一首吉他曲子,后来改编成浪漫的《国际歌》。那一刻我觉得——他是这部电影的合适作曲家:有人可以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歌曲转化为抒情浪漫的音乐。我也喜欢这种处理方式,特别是因为《国际歌》几乎出现在我所有的电影中,而且这次又以浪漫的吉他版本回归。表演遇见现实:克拉拉的乌苏拉和裸体男人 RC 张:克拉拉,我觉得你在这部电影中的存在很特别,你的表演也很出色。我想问一下你这次的拍摄体验如何?您之前的电影中有很多非专业演员。您对可乐感觉如何这次硼酸化?克拉拉:在桑格豪森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和那些实际住在那里并且也在电影中的人一起工作。我记得在桑格豪森和我们一起排练,就像电影中卖冰淇淋和薯条的那个人,那个向我问路去酒店的人,甚至是我角色的邻居——他们都来自那里。所以当我读剧本并走进电影中人物生活的环境时,我很惊讶地看到剧本通过他们改变了某些人和情况——他们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表演,而且非常契合。当然,我们也与专业演员合作,我认为 Mix 营造了非常好的氛围。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你不需要太多“表演”——你只是自然地对真实的互动做出反应。张RC:我也想问你和韩国演员合作是什么感觉,但他经常出现在朱利安的电影中。你可以分享你的有和他和他的孙子一起玩的经历吗?我在片子里感受到了一种很温暖的气氛,特别吸引人。这种组合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克拉拉:真的很好。韩国老演员李京泽是一位非常英俊的男人。有时候对他来说有点体力上的挑战,比如我们爬山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每天都带着自信的能量来到片场,他对我们很好奇,没有人能打扰他,总是说,“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还有他的孙子,他在电影中的角色叫Buk,但这实际上是他的真名。她非常美丽而且聪明。因为他是个孩子,所以每天只能设定几个小时,但他能准确地理解自己要做什么,而且学得很快,真是令人惊奇。朱利安:我想补充一点,我对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过程感到非常满意。在之前的项目中,我倾向于主要与专业演员合作,专业演员的比例每部电影中的专业演员都在增加。但我认为当专业演员和非专业演员相遇时会发生有趣的事情。专业演员必须对真实的人做出反应,这反过来又帮助了非专业演员——他们创造了一个环境,说:“现在我们在表演,这就是表演的空间。”这种相互作用很棒。它还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言语节奏。当然有局限性,但在这部电影中,我觉得我们真正达到了“最佳点”:利用非专业演员的魅力,同时也能够与专业演员深入合作,创造出只有训练有素的演员才能做到的精确时刻——这一切都是通过长时间的重新安排和打磨而实现的。对我来说,这一次确实是“两全其美”,我高兴极了。张RC:下一部电影你们还会合作吗?朱利安:我希望如此。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作过程——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克拉拉:让我补充一下前面的问题,穿着西装的酒店工作人员在片场真的很紧张。他一直在发抖,紧张得吃不下饭。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很特别。对我们来说,拍电影是日常生活,有时很困难,有时又很精彩。但看到有人对参与感到紧张,让我们意识到:这对于共同创造的团队来说确实意义重大。张RC:你是如何决定设置两个裸体男人的情节的?朱利安:很有趣,这是我们在中国问的问题。每当观众看到这两个裸体男人时,都会欢呼雀跃。事实上,德国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叫做FKK(Freikörperkultur,自由身体文化/自然主义/天体运动),它自20世纪初就存在,并在东德发展得尤其强劲。例如,在桑格豪森附近,有一条官方标记的“裸露徒步路线”——地图上明确写着“裸露徒步路线”“男人”是常见的在哈尔茨山脉。所以这不是我们发明的东西,而是一种真实的文化。张RC:我知道德国有很多裸体海滩。朱利安:是的,这是东德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也成为了一种刻板印象:“东德人是裸体的。” “所以我不想让一个东德人来扮演这两个裸体男人,而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因为我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如果我要开这个玩笑,我宁愿在我自己的国家开这个玩笑,而不是强化东德的刻板印象。这也是关于东德的陈词滥调。这两个男人有一种咄咄逼人的、令人不舒服的男性气质:亲密、感人,有点有毒,我们想要传达的不仅仅是裸体,而是男性的存在。本身《反暴力》的诗,也许我可以玩一些类似的东西。 张RC:你是故意在电影中选择非德国汽车吗?因为我注意到电影中有很多韩国现代汽车,而且只有韩国人开大众汽车,最后他把那辆车卖掉了。an: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说实话,只是用过我们在桑格豪森能找到的汽车。但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本应该假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我并没有真正思考过。其实,最搞笑的是:电影中的汽车经销店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名字其实是“狼车”,但它不是我们发明的,但商店实际上就是这么叫的。更可笑的是:我不太懂车。我以为是本田,演员在拍摄对白时也说了“本田”。然而,在混合后的过程中,有人说,“那不是本田——这是现代。” “所以音响工程师必须回到对话录音,找到一个‘E’元音,然后剪下音节并将它们插入到现代汽车中。他花了 20 分钟才更改品牌名称。一位当地人向该人士证实,我们告诉现代汽车是错误的。影片中汽车的经销店与沃尔夫斯堡或大众集团无关,而是其实叫“狼汽车经销商”是因为车主姓狼。张RC:为什么片中你要围绕德文字母“U(Wu)”开这么多玩笑?朱利安:对我来说,写作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事物。有时我觉得说话有点害羞,尤其是在制片人面前,因为我通常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好主意。有些人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概念,但我不是。我通常从一个有点愚蠢的想法开始,然后不断调整它,直到它变得更好。这就是电影中“U”的由来。当我写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可以插入一个“u”,所以我想:我可以再插入一点吗?结果,整个场景都是由它构建的。有时你会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然后去谷歌并发现新的东西。例如,我搜索是否有一个名为“UUE”的元素,结果是确实有——更有趣的是该元素的寿命非常短并且很快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和“短暂关系”的笑话联系起来。这就是我喜欢写作的原因——当你保持开放的心态时,那些偶然的事情就会构成你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像拍电影:你必须保持敏感,去观察和收集现实中发生的让你震惊的事情。事实往往比我们所经历的更有创意。 图像创意的传递:DFFB 和德国新电影技术 RC 张:您的许多长期合作者都在 DFFB 学习过。我想知道这所学校对您个人或职业有何影响?你能分享一些经验吗? Julian:对我来说,DFFB 在很多层面上都非常重要。我在校期间,学校经历了很多变化。刚进学校的时候制度还没有完善,但很快校长就换了,很多老师被解雇,还有一些人因不满而离开,所以学校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耳边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老师,Martin Martschewski,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有纪录片背景,会放映有趣的电影。他常说,电影应该像在森林里散步:你转过拐角,突然看到新的东西。电影不一定是线性叙事,它可以像散步一样展开。这个理念极大地影响了我,我想它也影响了我的一些同学。但最重要的是其他学生,比如我的制片人基里尔,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近十五年,还有亚历山大·科比里泽,他和我们在同一个导演班。他本来学了一年制作,然后转行做导演,所以又修了一年课程,我们就在同一个班认识了。班上还有来自瑞士的双胞胎导演Ramon Zürcher和Silvan Zürcher,他们也是和我们同班的。 Horse Max Linz 比我早一年入学,但是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们在柏林自由大学一起学习电影理论。当时在那里任教的人是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格特鲁德·科赫。她出身于法兰克福学派,是德国最早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之一。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当我申请林茨的 DFFB 时,我意识到:既然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可以申请,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以前没有电影背景。张RC:DFFB奖是一个正式的文凭吗?朱利安:是的,它没有学位。所以如果我们停止拍摄,我们的保险系统就会出现问题。但是本片中的伊朗摄影师法拉兹·费沙拉基(Faraz Fesharaki)也在那里学习过,所以我们仍然与学校的人密切合作——这种经验非常重要。张RC:你本科专业是电影理论。我想这也出现在你的电影中吧?朱利安:我不确定这是一件好事,这也是我对一个贱人的诅咒我有一个学院我很复杂,总是想知道“教授会怎么想?”我担任理论文本的翻译和编辑,其中包括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重要翻译课程。我的朋友京泽在撒谎,他总是在我的电影中扮演普通人的角色。他的儿子Sulgi Lie也是一位电影学者。他的新书《来吧。阿多诺的闹剧:查理·卓别林和马克思兄弟》写得很好。通过他们,我仍然觉得自己与电影理论有联系。 RC 张:Harun Farocki 对你有影响吗? Julian:严格来说,不是太直接或太激烈。但我记得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学校,或者行业和资助系统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做一些更接近商业电影的事情。不完全是好莱坞,但模仿商业美学的倾向是存在的。于是我们又开始重新审视DFFB以前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接触像法罗基这样的人让我们相信电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制作方式并且仍然很有趣。因为许多电影专业的学生试图制作一个五分钟的短片并使其看起来像一部价值百万美元的作品,而这种尝试往往注定会失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简单是可以的,想法比制作规模更重要,而且电影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平淡、深思熟虑的品质。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幽灵归来:托洛茨基与《资本论》 张RC:我也以为爱森斯坦本人尝试过电影《资本论》,但这个计划既雄心勃勃,最终也未能完成。您在之前的许多电影中都提到了资本。这个系列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项目的延续吗?因为在《德古拉》中,逃离德国城市的托洛茨基这个角色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选择,它立刻让我想起了爱森斯坦在《资本论》中未完成的尝试。朱利安:其实有一个著名的轶事。我曾经在电影《十月》中听说托洛茨基的角色最初包括在内,但后来托洛茨基的部分不得不被删除。我不确定这是否属实。我还在一本电影史书中读到,爱森斯坦为托洛茨基选的演员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的牙医,或者是与牙医类似的职业。令我感兴趣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牙医在银幕上变成了托洛茨基,这让我很感兴趣:爱森斯坦经常使用非专业演员,我很好奇这个演员是谁。这种好奇心是我最初的动力。然后我开始思考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一本小说,她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1930 年代非常受欢迎的苏联作家。埃伦伯格率先提出了“解冻期”的概念。他的一部有趣的作品《弗拉西克·赫罗伊兹万斯的一生》写于二十年代,这对于当时的苏联环境来说很不寻常,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在面对二十年代的宣言时崩溃了,并被问到为什么打喷嚏。他非常害怕,于是逃跑了,最后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出现在电视上我设置了。这部小说似乎也是对弗里茨·朗的电影《is the way》的讽刺,我受到了启发,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情节有共性。然后我想,如果有人在1920年代从苏联乘船去美国,他们可能会在德国停留。当时的船只经常沿着波罗的海沿岸航行。当时,穆尔瑙也在拍摄《诺斯费拉图》。所以我想也许这部电影会是爱森斯坦和穆瑙相遇的场景,就像《十月》和《诺斯费拉图》的交集一样。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混合物,我喜欢这个想法。张RC:您的电影中是否尝试过“描绘资本”?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渴望?朱利安:不完全是,因为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老实说,我不确定这样的事情是否真的能吸引我。我尊重爱森斯坦,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想看一部根据资本改编的电影。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智力有限的人,我感到困惑我又困惑又困惑,我该如何理解这个理论呢?真正讲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如何遭遇理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但也会让我更加困惑。所以我很注重这种私人关系。幽默新思维:基里尔的制作和非讽刺姿态 RC 张:基里尔,你和朱利安合作了很多年,应该被认为是他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你们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工作风格?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您的意见会影响工作的方向吗?基里尔:老实说,你不知道谁在影响谁。我们一直在谈论它,但我们很少有“你给了我这个想法”或“我决定了一会儿。昨天看起来重要的事情今天可能不相关。这就是创作过程。我们交谈并提供意见,但这不是制片人的“电影主导”,这是朱利安的电影,他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朱利安:是的,但有时他是必需品合作伙伴。当然,这取决于你问的是谁,但基里尔经常有有趣的想法。聊天时,你可以感受到哪些想法能引起共鸣,哪些想法不能产生共鸣;如果你和不信任的人一起做,你的创作就会被毁掉。我们讨论的价值在于交流想法:背景、主题、可能的情节、什么有趣、什么无聊。无需深入细节,只需看看是什么点亮了您的大脑即可。朱利安:比如两个裸体男人,基里尔一听就笑得很开心,我就知道这个笑话应该留在剧本里。如果没有人笑的话,可能已经被删除了。这部电影确实有一个具体的方面:基里尔建议我可以做这个领域的项目,因为碰巧他在那里有一家公司。起初我的反应是“这不是我的工作方式”。但后来我开始研究、探索该地区,并最终发现了这座城市,这个项目就诞生了。电影被称为“可能性的艺术”。就像爱森斯坦可以拍《O“十月革命”,因为今天是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拍十月革命,你就会得到支持。”这就是电影制作很多时候的运作方式。基里尔:是的,那个讨论不是“你必须在这里写剧本”,这只是一个邀请:这里有资源,有支持,也许我们可以比上次更快地前进,项目的规模可以更小,而且不必花五年的时间来筹集资金。RC张:你现在还对资金感到困惑吗?当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在苹果种植园工作过,但有时我感觉就像这样,如果我没有得到它,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因为我们制作的电影也没有赚钱。所以,我怎么说呢,就像从一个收获到下一个收获一样。独立电影制片人,如果写下这篇文章,我们就不安全了。g 没有得到批准,也许我不会真正摘苹果,但感觉是一样的:我们总是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希望事情能顺利进行。如果没有发生,你就得另找工作,任何可以满足的事情。张RC:您在很多电影中都运用了幽默。你认为幽默或喜剧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表演吗?朱利安:我被问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但我从来没有得到完美的答案。我其实不太喜欢讽刺。讽刺常常取笑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像一个互联网模因:有效,但不变。我喜欢的幽默的本质就像一种产生新态度的幽默,或者像卓别林那样,一种赋予弱者再次对抗强者的力量的幽默:一种更谦虚、更人性化的幽默。我不确定幽默本身是否具有政治性,但作为创作者和观众,我觉得幽默创造了一种平视的交流。当理论和政治太大、太沉重、太可怕时,幽默就很适合对他们来说是可行的。有时候幽默也是一种思考的表现:当我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时,那是因为我当时想到了一个想法:否则我不会意识到它很有趣。对我来说,幽默通常来自于将通常不会联系在一起的两件事联系起来,而且我喜欢意想不到的联系。伊藤可能不是显而易见的答案,但仍然可以这么说。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则包括照片或视频)由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注:以上内容(包括图片和视频,如有)由网易HAO用户上传发布,网易HAO为社交媒体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第七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昨天落下帷幕。 《桑格豪森的森苏特/七月魅影》(Sehnsucht in Sangerhausen / Phantoms of July)作为“金椰子奖”主竞赛单元评审团获奖影片之一,以独特的情感质感成为今年最受影迷观看和喜爱的新片之一。近十几年来,德国导演朱利安·拉德迈尔不断借鉴历史文献、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前卫电影传统,为当代德国电影构建了一条独特的思想路径。尤连的长期合作者兼制片人基里尔·克拉索夫斯基也出现在每次美学实验中,提供他的创意作品。女主角克拉拉·施温宁凭借上一部作品《美丽的地方》获得2023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节最佳女主角金豹奖。他是德国新一代演员中的耀眼面孔。当代德国电影研究者张超群(以下简称RC张)对三位主创(简称朱利安、克拉拉和基里尔)进行了万字的深度访谈。谈话从《Sehnsucht》和德国故乡桑格豪森(Sangehausen)的诸多传统开始,扩展到鬼魂、移民、托洛茨基、诺瓦利斯和爱森斯坦未完成的《资本论》计划。逐步揭示影片背后复杂的思想,系统审视搞笑又深思熟虑的整体创作过程。 “Sehnsucht”的修辞:德国浪漫主义与大众文化 RC 张:在《桑格豪森的Sehnsucht》标题中,“Sehnsucht”是一个非常特定于德国文化的词,无法准确翻译;而国际英文标题《七月幻影》则指向了一个略有不同、更加幽灵般的形象。 2006年,Valeska Glitzbach还拍摄了一部名为《Sehnsucht》(Sehnsucht)的电影,同样发生在德国东部。哈夫你看过这部电影吗?朱利安:所以,是的,我知道那部电影。瓦莱斯卡还被认为是柏林学派的院长,并在 DFFB 任教。我对他有一点了解。我也知道《渴望》这部电影,因为我在2006年左右开始拍电影,当时我搬到了柏林,开始学习电影。这些电影当时正好在电影院上映,我就是在那时开始接触它们的。张RC:您在这些电影中寻找什么样的“Sehnsucht”,它与纯粹的浪漫或怀旧欲望有何不同?朱利安:所以我认为它是由多种因素自然产生的。首先,我并没有打算拍一部关于《Sehnsucht》的电影,这并不是我最初的想法。但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创造的人物慢慢开始呈现出一种严峻的状态。然后我在研究的时候,很快就发现,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其实出生在桑格豪森附近的一个小镇,他就是你在德国想到的那个能写诗的作家。最常谈论“Sehnsucht”这个主题。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这将成为电影的主题。这样,我之前写的和这种地理背景上的联系就会自然地结合起来。另外,我并不特别介意Valeska的“向往”,因为“Sehnsucht”这个概念在德国很常见且众所周知,并不是一个很新奇的主题。我喜欢“Sehnsucht in Sangerhausen”这个标题的原因是因为它听起来像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它有轻微的流行、流行歌曲的品质,我认为这很有趣。这个词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含义。更严肃的层面上,我认为这可能与德国的一种政治欲望有关,比如对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渴望,对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的渴望,或者对超越资本主义剥削的生活的渴望。但也是一种更经典、更浪漫的感觉,就是想象没有哈维的另一种生活ng具体定义它是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类型的定义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中。我发现有趣的是,虽然“Sehnsucht”这个词可能有一点听起来流行、“廉价”的含义,但它实际上具有内在的政治潜力。 “我想去别的地方”这个非常普遍的愿望,实际上隐藏着一种对德国现有社会结构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当然,我不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政治来解决,它会保持沉默,但我喜欢的是这个词有一个现有的尺度,汇集了不同层次的感受和思考。我想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我在想的另一件事是我可能想在这部电影中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以前的电影更多的是一种图案化的布莱希特结构,或者更系统的、类似模型的结构。在那些电影中,有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感觉,但那并不重要。这次我想探索这些非常个人的情感,看看这些个人情感与政治问题有何关系。张RC:为什么国际片名不延续这种兴奋,而是用《幻影》?朱利安:然后是关于“幻影”这个名字的问题,正如你提到的,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词。在不同的国家你必须找到新的翻译方式。还有一个问题是“桑格豪森”这个地名太不为人所知,以至于人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小镇。名称 所以这是一种妥协。经销商和销售公司都表示这个标题很难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我认为“七月幻影”对于 mempromiso 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这有点遗憾,因为原始德文标题中明显的地理参考缺失了,而且我喜欢德文标题中的“Sehnsucht”让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在寻找什么。也许你是什么king在英语中是“幽灵”而不是具体的感觉。但我喜欢这种对比:七月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月份,每个人都成年了,而“幽灵”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七月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月份,所以也许“七月的幽灵”有某种有趣的层面。张RC:“在你看来,‘Sehnsucht’和‘Heimat’有不同吗?有一些说法认为这两种情感可以相似。但看了你的电影后,我觉得‘Heimat’不是那个概念,对吗?”朱利安: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确实是我不喜欢的浪漫德国派。这种浪漫主义最终成为德国本身的一部分——就像德国灵魂的“Sehnsucht”。我们的想法是将这种情感和浪漫主义从德国的概念中解放出来,让每个人,甚至移民、韩国人、伊朗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情感,而不是局限于德国灵魂的想法。这样我会更国际。从文本到场所:一条新的创作之路 张瑞成:您之前的作品,比如《Blutsauger》或者《一条资产阶级狗的自我批评》,与历史文本、马克思的资本、苏联文学和前卫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您第一次在“地方”工作。您如何描述这一变化?从桑格豪斯出发,您带来了哪些新东西?朱利安:是的,没错。我感受到了我以前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我可以复制自己并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并变得更糟,或者我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就像你说的,我以前都是从文本、非常抽象的概念开始,然后在现实中寻找抽象的概念。一致的东西。但这次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地方出发,一个小镇。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一条从物质到概念的路径。过去,我是从具体的物理现实开始,然后转向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对观众来说也更真实,比如我自己。其中有对诺瓦利斯的《蓝色花朵》的参考,但这些参考自然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我仍然对理论和理论问题感兴趣,但此时它们更多地是反思问题的工具,而不是首先的起点。张RC:同时,在写作过程中,这座城市是“正确的”还是你在剧本中重塑了你最初的愿景?小镇是从头开始重塑剧本吗?朱利安:是的,这绝对是真的。事实上,在我来到这个小镇之前,并没有剧本。当我来到这里时,整个事情就开始了,然后它就不断发展。通常,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镇,都会坐在咖啡馆里。我首先看到的都是女服务员,我想:在这样的小镇上,女服务员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然后我想,我来自柏林,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在这里遇到女服务员会怎么样?然后我注意到附近有一个音乐会场地,我想也许他们会成为音乐家或者某物。就这样,一切开始成形。我还记得米洛什·福尔曼的电影《Lásky Jedné Plavovlásky》(1965),讲述了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女人爱上了一位音乐家的故事。我想也许这里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故事。晚上晚些时候,我去了另一家披萨店,发现所有服务员都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北马其顿。在镇上散步时,我还看到阿富汗难民和越南移民居住在这里。这让我意识到很多关于东德的德国电影都没有表现这些移民的存在,就好像移民不存在了一样。即使在佩措尔德的电影中,你也几乎看不到不是德国人的人。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不是我生活的现实世界。 RC 张:这次看电影的时候,我特别被桑格豪森的雕像、纪念碑和公共雕塑所感动。它们似乎不仅仅是背景,而是像重新引用的现成文本,带有当地历史、政治和美学的痕迹。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意识地将这些雕像作为一种新的“引证系统”来替代以往作品中文学或理论文本的引用?朱利安: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市不再有原来的工业了,整个工业都消失了,经济因此陷入衰退,失业率很高,人们处境尴尬。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雕像似乎让我们想起了该工艺曾经辉煌的历史,它们带着一种幽灵般的存在,仿佛过去仍在荣耀现在。这些雕像并不是为了庆祝“美好的过去”,而是提醒我们过去的痕迹仍然存在于现在。 改写德国现实:前东德的移民与日常生活的鬼魂 RC 张:你把拍摄地点设定在前东德,我注意到影片中角色的母亲曾经在负责电影材料的德发工厂工作。这样的设置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朱利安:是的,桑格豪森附近有一家工厂叫奥尔沃胶片厂(东德胶片原料制造商),负责胶片材料的生产,这些胶片的应用非常广泛。我不确定它是否出口到苏联,但它为许多国家制造了胶片。有一本关于这家工厂的很好的书,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员工都是女性,而且当时的工作是手工的。阅读这些女性如何掌握自己的工作并在电影制作中培养出自豪感是很有趣的。我们的电影也是用胶片拍摄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向他们致敬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揭示了另一个层面——参与该项目的许多音乐家都来自西德,对东德电影文化并不了解。所以这个设置确实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例如,乌苏拉的父亲开玩笑说,东德电影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她母亲的心意。米斯特里和电影技巧。我非常喜欢这种在电影课堂上工作的视角,因为电影背后总有一些人在制作素材:不仅是导演和摄影师,而且这些工人也看不到。影片后来提到了一位女演员,但西德人并不知道她是谁。这也反映了今天的现实:这种文化的历史几乎无人知晓,西德人对东德文化兴趣不大。张RC:这部电影受到苏联或东欧集团电影的影响吗?朱利安:是的,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那就是基拉·穆拉托娃的《漫长的告别》(1971)。我们关注他如何使用相机——他的动作、移动、变焦和平移——令人着迷的是他要做的事情有多少:相机可以是静止的,但通过变焦和平移,他仍然能够创造出一种极其复杂的视觉语言。我们真的很佩服他的这种方法电影 - 在同一个镜头中从大型特写镜头转变为广角全景镜头,利用动作来创造惊喜、节奏和情感变化。这个方法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正在看的另一部作品是乌兹别克斯坦导演埃利尔·伊什穆哈梅多夫 (Elyer Ishmukhamedov) 的《兰宾》(Lambing, 1967)。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我们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电影语言,可以说,我们确实从它那里“偷”了一些东西。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乌兹别克电影很精彩,但伊什穆哈梅多夫的名字太难记了,我总是记不住,而软电影绝对值得一看——我强烈推荐它。张RC:我发现在你的很多电影中,音乐在章节变化之前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往往具有非常德国的交响乐的品质。看起来这部电影主要是由音乐组成的。 Footor 你选择了这首音乐吗?它们有什么隐喻意义吗?朱利安:在这部影片中,音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想用德国浪漫音乐,尤其是罗伯特·舒曼,他也来自东德,来自这个地区。但更重要的不是地点,而是我喜欢的钢琴曲的天真行为。它被称为“von Fremden Länder und Menschen”(von Fremden Länder und Menschen),是舒曼的“Kinderszen”(童年场景)的开篇章节。就像一个孩子想象着遥远的地方,想象着陌生的人,想象着另一种世界——我觉得这种氛围很适合这部电影。它很简单,但却具有深厚的情感深度,我喜欢这种平衡。另外,为了与“德国高雅艺术”、古典音乐形成对比,我还想要一些具有类似情绪但格式相同的流行歌曲。我们找到了真实存在的当地民歌,甚至是关于我们拍摄的小镇的歌曲,我们把它们收集起来。我发现这种对比特别有趣,我喜欢这种方法。后来,我直觉地觉得需要一些更神秘的东西。我想到了笛子,因为在仙女中,笛子常常象征着魔法师c,就像在某个地方打电话给你。我偶然听到了日本作曲家武光彻的一首作品,觉得非常完美。起初我很担心,我对这首音乐到底了解多少?这有道理吗?但后来我发现他还有我们用过的另一首曲子,那是一首吉他曲子,后来改编成浪漫的《国际歌》。那一刻我觉得——他是这部电影的合适作曲家:有人可以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歌曲转化为抒情浪漫的音乐。我也喜欢这种处理方式,特别是因为《国际歌》几乎出现在我所有的电影中,而且这次又以浪漫的吉他版本回归。表演遇见现实:克拉拉的乌苏拉和裸体男人 RC 张:克拉拉,我觉得你在这部电影中的存在很特别,你的表演也很出色。我想问一下你这次的拍摄体验如何?您之前的电影中有很多非专业演员。您对可乐感觉如何这次硼酸化?克拉拉:在桑格豪森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和那些实际住在那里并且也在电影中的人一起工作。我记得在桑格豪森和我们一起排练,就像电影中卖冰淇淋和薯条的那个人,那个向我问路去酒店的人,甚至是我角色的邻居——他们都来自那里。所以当我读剧本并走进电影中人物生活的环境时,我很惊讶地看到剧本通过他们改变了某些人和情况——他们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表演,而且非常契合。当然,我们也与专业演员合作,我认为 Mix 营造了非常好的氛围。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你不需要太多“表演”——你只是自然地对真实的互动做出反应。张RC:我也想问你和韩国演员合作是什么感觉,但他经常出现在朱利安的电影中。你可以分享你的有和他和他的孙子一起玩的经历吗?我在片子里感受到了一种很温暖的气氛,特别吸引人。这种组合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克拉拉:真的很好。韩国老演员李京泽是一位非常英俊的男人。有时候对他来说有点体力上的挑战,比如我们爬山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每天都带着自信的能量来到片场,他对我们很好奇,没有人能打扰他,总是说,“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还有他的孙子,他在电影中的角色叫Buk,但这实际上是他的真名。她非常美丽而且聪明。因为他是个孩子,所以每天只能设定几个小时,但他能准确地理解自己要做什么,而且学得很快,真是令人惊奇。朱利安:我想补充一点,我对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过程感到非常满意。在之前的项目中,我倾向于主要与专业演员合作,专业演员的比例每部电影中的专业演员都在增加。但我认为当专业演员和非专业演员相遇时会发生有趣的事情。专业演员必须对真实的人做出反应,这反过来又帮助了非专业演员——他们创造了一个环境,说:“现在我们在表演,这就是表演的空间。”这种相互作用很棒。它还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言语节奏。当然有局限性,但在这部电影中,我觉得我们真正达到了“最佳点”:利用非专业演员的魅力,同时也能够与专业演员深入合作,创造出只有训练有素的演员才能做到的精确时刻——这一切都是通过长时间的重新安排和打磨而实现的。对我来说,这一次确实是“两全其美”,我高兴极了。张RC:下一部电影你们还会合作吗?朱利安:我希望如此。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作过程——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克拉拉:让我补充一下前面的问题,穿着西装的酒店工作人员在片场真的很紧张。他一直在发抖,紧张得吃不下饭。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很特别。对我们来说,拍电影是日常生活,有时很困难,有时又很精彩。但看到有人对参与感到紧张,让我们意识到:这对于共同创造的团队来说确实意义重大。张RC:你是如何决定设置两个裸体男人的情节的?朱利安:很有趣,这是我们在中国问的问题。每当观众看到这两个裸体男人时,都会欢呼雀跃。事实上,德国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叫做FKK(Freikörperkultur,自由身体文化/自然主义/天体运动),它自20世纪初就存在,并在东德发展得尤其强劲。例如,在桑格豪森附近,有一条官方标记的“裸露徒步路线”——地图上明确写着“裸露徒步路线”“男人”是常见的在哈尔茨山脉。所以这不是我们发明的东西,而是一种真实的文化。张RC:我知道德国有很多裸体海滩。朱利安:是的,这是东德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也成为了一种刻板印象:“东德人是裸体的。” “所以我不想让一个东德人来扮演这两个裸体男人,而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因为我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如果我要开这个玩笑,我宁愿在我自己的国家开这个玩笑,而不是强化东德的刻板印象。这也是关于东德的陈词滥调。这两个男人有一种咄咄逼人的、令人不舒服的男性气质:亲密、感人,有点有毒,我们想要传达的不仅仅是裸体,而是男性的存在。本身《反暴力》的诗,也许我可以玩一些类似的东西。 张RC:你是故意在电影中选择非德国汽车吗?因为我注意到电影中有很多韩国现代汽车,而且只有韩国人开大众汽车,最后他把那辆车卖掉了。an: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说实话,只是用过我们在桑格豪森能找到的汽车。但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本应该假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我并没有真正思考过。其实,最搞笑的是:电影中的汽车经销店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名字其实是“狼车”,但它不是我们发明的,但商店实际上就是这么叫的。更可笑的是:我不太懂车。我以为是本田,演员在拍摄对白时也说了“本田”。然而,在混合后的过程中,有人说,“那不是本田——这是现代。” “所以音响工程师必须回到对话录音,找到一个‘E’元音,然后剪下音节并将它们插入到现代汽车中。他花了 20 分钟才更改品牌名称。一位当地人向该人士证实,我们告诉现代汽车是错误的。影片中汽车的经销店与沃尔夫斯堡或大众集团无关,而是其实叫“狼汽车经销商”是因为车主姓狼。张RC:为什么片中你要围绕德文字母“U(Wu)”开这么多玩笑?朱利安:对我来说,写作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事物。有时我觉得说话有点害羞,尤其是在制片人面前,因为我通常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好主意。有些人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概念,但我不是。我通常从一个有点愚蠢的想法开始,然后不断调整它,直到它变得更好。这就是电影中“U”的由来。当我写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可以插入一个“u”,所以我想:我可以再插入一点吗?结果,整个场景都是由它构建的。有时你会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然后去谷歌并发现新的东西。例如,我搜索是否有一个名为“UUE”的元素,结果是确实有——更有趣的是该元素的寿命非常短并且很快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和“短暂关系”的笑话联系起来。这就是我喜欢写作的原因——当你保持开放的心态时,那些偶然的事情就会构成你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像拍电影:你必须保持敏感,去观察和收集现实中发生的让你震惊的事情。事实往往比我们所经历的更有创意。 图像创意的传递:DFFB 和德国新电影技术 RC 张:您的许多长期合作者都在 DFFB 学习过。我想知道这所学校对您个人或职业有何影响?你能分享一些经验吗? Julian:对我来说,DFFB 在很多层面上都非常重要。我在校期间,学校经历了很多变化。刚进学校的时候制度还没有完善,但很快校长就换了,很多老师被解雇,还有一些人因不满而离开,所以学校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耳边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老师,Martin Martschewski,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有纪录片背景,会放映有趣的电影。他常说,电影应该像在森林里散步:你转过拐角,突然看到新的东西。电影不一定是线性叙事,它可以像散步一样展开。这个理念极大地影响了我,我想它也影响了我的一些同学。但最重要的是其他学生,比如我的制片人基里尔,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近十五年,还有亚历山大·科比里泽,他和我们在同一个导演班。他本来学了一年制作,然后转行做导演,所以又修了一年课程,我们就在同一个班认识了。班上还有来自瑞士的双胞胎导演Ramon Zürcher和Silvan Zürcher,他们也是和我们同班的。 Horse Max Linz 比我早一年入学,但是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们在柏林自由大学一起学习电影理论。当时在那里任教的人是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格特鲁德·科赫。她出身于法兰克福学派,是德国最早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之一。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当我申请林茨的 DFFB 时,我意识到:既然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可以申请,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以前没有电影背景。张RC:DFFB奖是一个正式的文凭吗?朱利安:是的,它没有学位。所以如果我们停止拍摄,我们的保险系统就会出现问题。但是本片中的伊朗摄影师法拉兹·费沙拉基(Faraz Fesharaki)也在那里学习过,所以我们仍然与学校的人密切合作——这种经验非常重要。张RC:你本科专业是电影理论。我想这也出现在你的电影中吧?朱利安:我不确定这是一件好事,这也是我对一个贱人的诅咒我有一个学院我很复杂,总是想知道“教授会怎么想?”我担任理论文本的翻译和编辑,其中包括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重要翻译课程。我的朋友京泽在撒谎,他总是在我的电影中扮演普通人的角色。他的儿子Sulgi Lie也是一位电影学者。他的新书《来吧。阿多诺的闹剧:查理·卓别林和马克思兄弟》写得很好。通过他们,我仍然觉得自己与电影理论有联系。 RC 张:Harun Farocki 对你有影响吗? Julian:严格来说,不是太直接或太激烈。但我记得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学校,或者行业和资助系统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做一些更接近商业电影的事情。不完全是好莱坞,但模仿商业美学的倾向是存在的。于是我们又开始重新审视DFFB以前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接触像法罗基这样的人让我们相信电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制作方式并且仍然很有趣。因为许多电影专业的学生试图制作一个五分钟的短片并使其看起来像一部价值百万美元的作品,而这种尝试往往注定会失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简单是可以的,想法比制作规模更重要,而且电影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平淡、深思熟虑的品质。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幽灵归来:托洛茨基与《资本论》 张RC:我也以为爱森斯坦本人尝试过电影《资本论》,但这个计划既雄心勃勃,最终也未能完成。您在之前的许多电影中都提到了资本。这个系列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项目的延续吗?因为在《德古拉》中,逃离德国城市的托洛茨基这个角色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选择,它立刻让我想起了爱森斯坦在《资本论》中未完成的尝试。朱利安:其实有一个著名的轶事。我曾经在电影《十月》中听说托洛茨基的角色最初包括在内,但后来托洛茨基的部分不得不被删除。我不确定这是否属实。我还在一本电影史书中读到,爱森斯坦为托洛茨基选的演员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的牙医,或者是与牙医类似的职业。令我感兴趣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牙医在银幕上变成了托洛茨基,这让我很感兴趣:爱森斯坦经常使用非专业演员,我很好奇这个演员是谁。这种好奇心是我最初的动力。然后我开始思考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一本小说,她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1930 年代非常受欢迎的苏联作家。埃伦伯格率先提出了“解冻期”的概念。他的一部有趣的作品《弗拉西克·赫罗伊兹万斯的一生》写于二十年代,这对于当时的苏联环境来说很不寻常,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在面对二十年代的宣言时崩溃了,并被问到为什么打喷嚏。他非常害怕,于是逃跑了,最后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出现在电视上我设置了。这部小说似乎也是对弗里茨·朗的电影《is the way》的讽刺,我受到了启发,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情节有共性。然后我想,如果有人在1920年代从苏联乘船去美国,他们可能会在德国停留。当时的船只经常沿着波罗的海沿岸航行。当时,穆尔瑙也在拍摄《诺斯费拉图》。所以我想也许这部电影会是爱森斯坦和穆瑙相遇的场景,就像《十月》和《诺斯费拉图》的交集一样。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混合物,我喜欢这个想法。张RC:您的电影中是否尝试过“描绘资本”?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渴望?朱利安:不完全是,因为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老实说,我不确定这样的事情是否真的能吸引我。我尊重爱森斯坦,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想看一部根据资本改编的电影。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智力有限的人,我感到困惑我又困惑又困惑,我该如何理解这个理论呢?真正讲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如何遭遇理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但也会让我更加困惑。所以我很注重这种私人关系。幽默新思维:基里尔的制作和非讽刺姿态 RC 张:基里尔,你和朱利安合作了很多年,应该被认为是他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你们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工作风格?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您的意见会影响工作的方向吗?基里尔:老实说,你不知道谁在影响谁。我们一直在谈论它,但我们很少有“你给了我这个想法”或“我决定了一会儿。昨天看起来重要的事情今天可能不相关。这就是创作过程。我们交谈并提供意见,但这不是制片人的“电影主导”,这是朱利安的电影,他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朱利安:是的,但有时他是必需品合作伙伴。当然,这取决于你问的是谁,但基里尔经常有有趣的想法。聊天时,你可以感受到哪些想法能引起共鸣,哪些想法不能产生共鸣;如果你和不信任的人一起做,你的创作就会被毁掉。我们讨论的价值在于交流想法:背景、主题、可能的情节、什么有趣、什么无聊。无需深入细节,只需看看是什么点亮了您的大脑即可。朱利安:比如两个裸体男人,基里尔一听就笑得很开心,我就知道这个笑话应该留在剧本里。如果没有人笑的话,可能已经被删除了。这部电影确实有一个具体的方面:基里尔建议我可以做这个领域的项目,因为碰巧他在那里有一家公司。起初我的反应是“这不是我的工作方式”。但后来我开始研究、探索该地区,并最终发现了这座城市,这个项目就诞生了。电影被称为“可能性的艺术”。就像爱森斯坦可以拍《O“十月革命”,因为今天是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拍十月革命,你就会得到支持。”这就是电影制作很多时候的运作方式。基里尔:是的,那个讨论不是“你必须在这里写剧本”,这只是一个邀请:这里有资源,有支持,也许我们可以比上次更快地前进,项目的规模可以更小,而且不必花五年的时间来筹集资金。RC张:你现在还对资金感到困惑吗?当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在苹果种植园工作过,但有时我感觉就像这样,如果我没有得到它,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因为我们制作的电影也没有赚钱。所以,我怎么说呢,就像从一个收获到下一个收获一样。独立电影制片人,如果写下这篇文章,我们就不安全了。g 没有得到批准,也许我不会真正摘苹果,但感觉是一样的:我们总是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希望事情能顺利进行。如果没有发生,你就得另找工作,任何可以满足的事情。张RC:您在很多电影中都运用了幽默。你认为幽默或喜剧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表演吗?朱利安:我被问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但我从来没有得到完美的答案。我其实不太喜欢讽刺。讽刺常常取笑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像一个互联网模因:有效,但不变。我喜欢的幽默的本质就像一种产生新态度的幽默,或者像卓别林那样,一种赋予弱者再次对抗强者的力量的幽默:一种更谦虚、更人性化的幽默。我不确定幽默本身是否具有政治性,但作为创作者和观众,我觉得幽默创造了一种平视的交流。当理论和政治太大、太沉重、太可怕时,幽默就很适合对他们来说是可行的。有时候幽默也是一种思考的表现:当我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时,那是因为我当时想到了一个想法:否则我不会意识到它很有趣。对我来说,幽默通常来自于将通常不会联系在一起的两件事联系起来,而且我喜欢意想不到的联系。伊藤可能不是显而易见的答案,但仍然可以这么说。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则包括照片或视频)由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注:以上内容(包括图片和视频,如有)由网易HAO用户上传发布,网易HAO为社交媒体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下一篇:没有了